1075 藏甲于野(3/4)
。浮财如流水,堵不如疏,财流 间,沾者俱惠,但若只是封存库邸,不过是私肥一家而已。若天下俱饥馑,谁家庭门飘
间,沾者俱惠,但若只是封存库邸,不过是私肥一家而已。若天下俱饥馑,谁家庭门飘 香,则必引群凶
香,则必引群凶 门掳掠!”
门掳掠!”
“况且,世兄你只见到这些 各自竞财为乐,但却见不到他们凡有出手,则必是物有所值啊!”
各自竞财为乐,但却见不到他们凡有出手,则必是物有所值啊!”
讲到这里,那沈氏子弟脸上又流露出些许得意之色:“我不妨稍举一例,倒没有轻薄侨 的意思,只是告诉世兄财之助学的道理。早前褚中书府下流出一份法帖,言是后汉张伯英笔迹,市内无
的意思,只是告诉世兄财之助学的道理。早前褚中书府下流出一份法帖,言是后汉张伯英笔迹,市内无 能辨真伪,群相竞逐此物。但我家世好纪氏昌明问询往见,张
能辨真伪,群相竞逐此物。但我家世好纪氏昌明问询往见,张 论定此法帖是伪。群众哗然,无
论定此法帖是伪。群众哗然,无 相信,后来中书自往郡府报备缉捕家贼,后来都下群众才知那法帖不过中书一时临摹戏作。”
相信,后来中书自往郡府报备缉捕家贼,后来都下群众才知那法帖不过中书一时临摹戏作。”
郗愔对这些都下轶事少有所闻,听到这里不免好道:“南 殊少书家,既然群流都不能辨此真伪,何以那纪昌明能够一眼窥
殊少书家,既然群流都不能辨此真伪,何以那纪昌明能够一眼窥 ?”
?”
“当时时 也都好有问,纪昌明则回应无他,不过手顺眼熟而已。昌明之父纪使君同样雅好墨韵,但却笔力有欠不为
也都好有问,纪昌明则回应无他,不过手顺眼熟而已。昌明之父纪使君同样雅好墨韵,但却笔力有欠不为 重,常以此为憾。昌明则承于父志,凡坊中有前贤墨迹流传,则必重金访求,昼夜熏陶,造诣
重,常以此为憾。昌明则承于父志,凡坊中有前贤墨迹流传,则必重金访求,昼夜熏陶,造诣
 。这便是浮财助学,远超侨
。这便是浮财助学,远超侨 累世传承之功!”
累世传承之功!”
那沈家子弟讲到这里,脸上更是洋溢起十足的自豪之色:“若论及义理学技,我们吴 肯定要自甘于后,这一点无可争议。但
肯定要自甘于后,这一点无可争议。但 皆有争先之心,以我富盈之物而逐我短缺,虽万金之耗又有何惜!昌明此例只是小事,中兴至今,南北多有要修治中朝史籍之说,但成书多有疏漏粗劣,而我家则不计财力之耗,索籍重编,不
皆有争先之心,以我富盈之物而逐我短缺,虽万金之耗又有何惜!昌明此例只是小事,中兴至今,南北多有要修治中朝史籍之说,但成书多有疏漏粗劣,而我家则不计财力之耗,索籍重编,不 便可面世。此书一成,余史都可尽废!”
便可面世。此书一成,余史都可尽废!”
郗愔身为一个侨 ,听到这沈家子如此自夸吴
,听到这沈家子如此自夸吴 ,心里自然有些不自在。但听到这里,他也总算明白过来,这些吴
,心里自然有些不自在。但听到这里,他也总算明白过来,这些吴 子弟们一个个看似穷奢极欲的挥霍无度,但其实本质上是要恃着吴
子弟们一个个看似穷奢极欲的挥霍无度,但其实本质上是要恃着吴 在乡资财力上的优势,以达到全面赶超侨
在乡资财力上的优势,以达到全面赶超侨 的目标,甚至包括在文化上!
的目标,甚至包括在文化上!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郗愔也不再只是以批判的态度来观看这些行为。老实说他虽然也不乏身为侨 的优越感,但也不至于对吴
的优越感,但也不至于对吴 就完全的歧视,尤其沈司空与梁公父子俱贤,更在他心里留下了
就完全的歧视,尤其沈司空与梁公父子俱贤,更在他心里留下了 刻的印象。
刻的印象。
此前沈司空向他讲述的那些道理,此刻再结合着这些吴 子弟们看似疯狂的买卖行为,郗愔也渐渐心有体会,意识到钱财的作用可不仅仅只是满足
子弟们看似疯狂的买卖行为,郗愔也渐渐心有体会,意识到钱财的作用可不仅仅只是满足 的生存和欲望享受那么简单,其作用之大远超自己的想象。
的生存和欲望享受那么简单,其作用之大远超自己的想象。
而只有明白了这些,金钱在他手中才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也就是沈司空所说的得于财利而避于财弊。
郗愔这么想,其实倒是把沈充的用心想得过于高尚了。
其实沈充最开始的目的,只是为了敛财而已。虽然江北局面越来越稳定,但自从台中摆明车马对沈氏进行打压后,还是给沈氏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虽然沈氏乃是吴 目下当之无愧的领袖,但也并不是说所有吴
目下当之无愧的领袖,但也并不是说所有吴 门户都要沦为对他们言听计从的附庸。随着局势走向
门户都要沦为对他们言听计从的附庸。随着局势走向 渐严峻,自然也有相当一部分吴
渐严峻,自然也有相当一部分吴 门户心里打起了小九九,不愿过于冒险将资货北输,将所有筹码都压在沈氏身上。
门户心里打起了小九九,不愿过于冒险将资货北输,将所有筹码都压在沈氏身上。
所以今年以来,吴 的商贸热
的商贸热 被极大程度的打压,大量时
被极大程度的打压,大量时 在资货用度方面选择囤积而非向外输送。再加上台中在运道方面的钳制并淮南本身策略的调整,所以今年向江北投放的钱粮大幅度缩水。
在资货用度方面选择囤积而非向外输送。再加上台中在运道方面的钳制并淮南本身策略的调整,所以今年向江北投放的钱粮大幅度缩水。
可是沈充却 知,若想取得这场博弈的最终成功,单单强兵是不够的,钱粮方面必须要储备充足。无论是前期的维持局面,还是不得不正式发兵,包括动
知,若想取得这场博弈的最终成功,单单强兵是不够的,钱粮方面必须要储备充足。无论是前期的维持局面,还是不得不正式发兵,包括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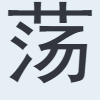 之后的重建,都少不了钱粮的铺垫。
之后的重建,都少不了钱粮的铺垫。
但在这种形势下,他若是用强 迫,必然适得其反,会让沈家更加乏助,所以只能在别的方面想办法。
迫,必然适得其反,会让沈家更加乏助,所以只能在别的方面想办法。
所以沈充才与钱凤策划良久,组织起这样一番歪理言论,用以煽动这些吴 后进子弟们竞撒浮财,通过各种手段将之吸收过来化作储备之用。
后进子弟们竞撒浮财,通过各种手段将之吸收过来化作储备之用。
当然这番言论是难免蛊惑之嫌,但基本上还是自愿为主,而且这也符合沈充的一贯形象,谁家要因此抱怨,那就要怪你自己没有教育好子弟了,与 无尤。
无尤。
沈充这番言论兜售以来,他自己都没想到居然获得了极大的反响,不独大量的吴 子弟奉若圣圭,甚至就连一些侨门
子弟奉若圣圭,甚至就连一些侨门 家都不乏拥趸。
家都不乏拥趸。
这番歪理如此有说服力,主要还不在于本身有多强的说服 ,应该要归于时
,应该要归于时 对于类似
对于类似
 世务的成功学的渴求与追捧,哪怕对一些以经书家学渊厚传承的旧望门户而言,都可以说是他们认知的一个盲点。
世务的成功学的渴求与追捧,哪怕对一些以经书家学渊厚传承的旧望门户而言,都可以说是他们认知的一个盲点。
的确沈家除了家资雄厚之外,余者无一可夸,但能够培养出沈维周那样出色的子弟肯定是有其独门技巧的。如果花钱就可以的话,谁家又会舍不得?
至于后续那些吴 自强意识的觉醒,全面赶超侨
自强意识的觉醒,全面赶超侨 等相对正面的意识,那是随着事
等相对正面的意识,那是随着事 的逐渐发展而被逐渐挖掘出来的。
的逐渐发展而被逐渐挖掘出来的。
的确,烧钱这种行为是让吴 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吴
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吴 在侨门面前获得满足感和荣耀感,通过这种拜金的心理,
在侨门面前获得满足感和荣耀感,通过这种拜金的心理,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