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海残花录,修整版(8)(6/13)
哼了声,点 说:“舰炮和步枪没问题,火药和铁轨也能凑齐。吗啡和鸦片酊紧俏,得从黑市调。”
说:“舰炮和步枪没问题,火药和铁轨也能凑齐。吗啡和鸦片酊紧俏,得从黑市调。”
他声音低下来,“这些货的少说也要10天后凑齐,舰炮的装船可能更慢,你告诉两位船长,由于舰炮的高度敏感 ,需要晚上装船,到时候船上得留
,需要晚上装船,到时候船上得留 配合。海关的事我摆平,你别
配合。海关的事我摆平,你别 跑,北方佬的眼线多。”
跑,北方佬的眼线多。”
离开普列纹商会时,我路过一排办公桌,一个文书低 抄写,他抬
抄写,他抬 了我一眼,手快得像条蛇,塞给我一个小皮包,沉甸甸的像装了石
了我一眼,手快得像条蛇,塞给我一个小皮包,沉甸甸的像装了石 。他
。他 也不抬,自言自语地嘀咕:“海鸥之家,2楼6房,包里有
也不抬,自言自语地嘀咕:“海鸥之家,2楼6房,包里有 住凭据,房费付了一部分,剩下你自己续。”声音低得像蚊子哼,像是怕隔墙有耳。我心
住凭据,房费付了一部分,剩下你自己续。”声音低得像蚊子哼,像是怕隔墙有耳。我心 一紧,抓紧皮包,低声回了
一紧,抓紧皮包,低声回了
句:“谢了,兄弟。”他没吭声,笔尖划得纸哗哗响,像啥也没发生。 出了商会,布特尔的夜风凉得刺骨,巷子里的铜灯晃着暗光,石板路湿漉漉的,映出靴子的黑影。我低 裹紧大衣,皮包塞在内兜,沉得像块铁,我猜里
裹紧大衣,皮包塞在内兜,沉得像块铁,我猜里 八成是此行报酬和房间信息。
八成是此行报酬和房间信息。
我没做多想直奔布莱克钟表行,这里还是老样子,橱窗里摆着几块怀表,指针在汽灯下闪着冷光。推门进去,柜台上堆着齿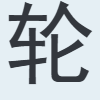 和螺丝,接待的还是上次那个伪装成钟表师傅的家伙,他抬
和螺丝,接待的还是上次那个伪装成钟表师傅的家伙,他抬 看我一眼,又继续低
看我一眼,又继续低 修表说:“又是你,萨凡纳来的。”我点点
修表说:“又是你,萨凡纳来的。”我点点 ,压低帽檐,低声说:“找坎伯兰,布朗的货。”
,压低帽檐,低声说:“找坎伯兰,布朗的货。”
他没废话,领我穿过后门,进了个小隔间,木墙 得发霉,油灯晃得影子像鬼。里
得发霉,油灯晃得影子像鬼。里 坐着个新面孔,自称坎伯兰,梅森先生的助手。三十来岁,穿灰呢西装,脸白得像没晒过太阳,眼神尖得像针。他指了指椅子,声音
坐着个新面孔,自称坎伯兰,梅森先生的助手。三十来岁,穿灰呢西装,脸白得像没晒过太阳,眼神尖得像针。他指了指椅子,声音 得像嚼纸:“莫林,坐,东西拿出来。”
得像嚼纸:“莫林,坐,东西拿出来。”
我从怀里掏出雪茄盒,坎伯兰接过去,眯眼翻了翻,递给我一张收据,他靠回椅背,椅子吱吱响,低声说:“这次别急着走,11月20 你到这个地方来找我,
你到这个地方来找我,
我会给你新的指示。”他说着又给我写了张纸条。
我收下纸条,试探着问:“啥指示?”
他摆摆手:“到时候就知道,少问,少麻烦。出去吧。”
我没再吭声,起身推门,铃铛又叮当一响,钟表师傅瞅了我一眼,低 继续磨齿
继续磨齿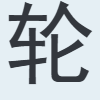 ,像啥也没听见。出了钟表行,夜风卷着煤烟味,巷子暗得像锅底,油灯晃得影子
,像啥也没听见。出了钟表行,夜风卷着煤烟味,巷子暗得像锅底,油灯晃得影子 跳。我低
跳。我低 快步往海鸥之家走。值得欣慰的是这次没发现明显在盯着我的
快步往海鸥之家走。值得欣慰的是这次没发现明显在盯着我的 ,海鸥之家里我隔壁的监听者好像也撤了,也没提要求我出门再打报告的。 但这可能只是对我更大的试探,极有可能是外松内紧,但管他呢,能透
,海鸥之家里我隔壁的监听者好像也撤了,也没提要求我出门再打报告的。 但这可能只是对我更大的试探,极有可能是外松内紧,但管他呢,能透 气真好。
气真好。
按那几个洗衣工告诉我的,利物浦的华 社区挤在皮特街旁的一条小巷,房屋低矮,砖墙熏得发黑,门框上贴着褪色的红对联,十分狭窄,据说这里住着百来个中国
社区挤在皮特街旁的一条小巷,房屋低矮,砖墙熏得发黑,门框上贴着褪色的红对联,十分狭窄,据说这里住着百来个中国 ,几家铺子挤在一起,门
,几家铺子挤在一起,门 挂着
挂着 布帘,卖卤鸭
布帘,卖卤鸭 和粥的摊子冒着白汽,一个老汉裹着
和粥的摊子冒着白汽,一个老汉裹着 棉袄,蹲在墙角抽旱烟,烟雾白如棉纱,嘴里嘀咕着福建话,抱怨工钱被克扣。
棉袄,蹲在墙角抽旱烟,烟雾白如棉纱,嘴里嘀咕着福建话,抱怨工钱被克扣。
我溜进一家叫“聚福”的小餐馆,木招牌裂了道 子。里
子。里 就三张桌子,油腻得发亮,墙上贴着张关公像,香炉
就三张桌子,油腻得发亮,墙上贴着张关公像,香炉 着两炷细香,烟袅袅得像叹气。老板是个五十来岁的福建
着两炷细香,烟袅袅得像叹气。老板是个五十来岁的福建 ,脸瘦得像
,脸瘦得像 柴,棉衫补了几个补丁,
柴,棉衫补了几个补丁, 着夹生英语问我要啥。我点了
着夹生英语问我要啥。我点了
一壶清茶,店主提来一个瓦罐茶壶,国内一壶几文钱,这儿要一先令,想想也是英国不产茶叶,得靠船运。
旁边桌坐了个华 水手,带着个白
水手,带着个白

 ,俩
,俩 低声聊着,桌上摆着几碟小菜,水手二十多岁,皮肤晒得黝黑,广东
低声聊着,桌上摆着几碟小菜,水手二十多岁,皮肤晒得黝黑,广东 音。白
音。白

 三十多岁,身材像根毛笔,棕发
三十多岁,身材像根毛笔,棕发 糟糟地扎着,棉裙磨得发白,脸颊有几块雀斑,手指上戴枚磨旧的金戒指,在油灯下闪着暗光。我瞧得新奇,端着茶杯凑过去,用英语搭话:“兄弟,你们这组合少见,咋认识的?”
糟糟地扎着,棉裙磨得发白,脸颊有几块雀斑,手指上戴枚磨旧的金戒指,在油灯下闪着暗光。我瞧得新奇,端着茶杯凑过去,用英语搭话:“兄弟,你们这组合少见,咋认识的?”
水手瞅了我一眼,笑了一下,露出一颗缺牙:“我叫阿财,跑船六年,她叫夏莉,四年前在码 洗衣摊认识的。”
洗衣摊认识的。”
夏莉声音细得像叹气:“我娘死了,丈夫也死了,厂里工钱不够吃,他肯娶我。”
阿财叹 气说:“英国佬对我们两个都很不待见,邻里叫她‘中国佬的婊子’,连教堂都不让她进。我们搬到皮特街,省着点也能过。”
气说:“英国佬对我们两个都很不待见,邻里叫她‘中国佬的婊子’,连教堂都不让她进。我们搬到皮特街,省着点也能过。”
他指指莉莉的戒指,“这戒指是我攒一年工钱买的,她戴着没摘过。” 由于我听不懂他的广东 音,我们全程用英语对话。
音,我们全程用英语对话。
我和阿财又闲聊几句,正要离开,一个 把手放在我肩上,说了句北方
把手放在我肩上,说了句北方 音的汉语:“想不到你还没死,跑到这里做什么。”
音的汉语:“想不到你还没死,跑到这里做什么。”
我回 一看,感到一阵惊喜:“陈大器!!”
一看,感到一阵惊喜:“陈大器!!”
这 正是当初在洋行带我
正是当初在洋行带我 行的同僚,也是我从小玩不到的好朋友,他也要了壶茶,说自己这次也是奉命出洋,偶然遇到,现在朝廷逐渐重视起洋务来,出洋采买的
行的同僚,也是我从小玩不到的好朋友,他也要了壶茶,说自己这次也是奉命出洋,偶然遇到,现在朝廷逐渐重视起洋务来,出洋采买的 比以前多了不少。
比以前多了不少。
我们不禁聊起了往事,一直说到1859年的那次出洋,我把当初我遇到的 况和盘托
况和盘托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